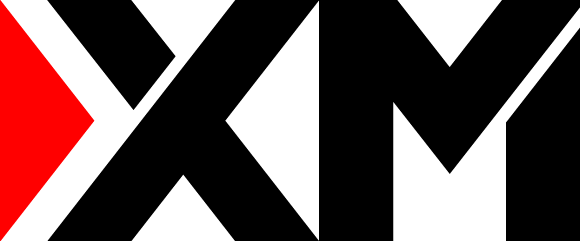让我们从基础知识开始:国会授权资金用于一系列定义政府角色的举措。同时,国会制定税收规定来确定政府的税收额。然而,这两项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开来的,导致了征收与支出之间的不匹配。当税收收入不足以支付支出时,我们就会出现赤字;反之,当税收超过支出时,我们就会实现盈余。
债务是赤字的累积结果。换句话说,赤字会增加债务,而盈余会减少债务。为了举例说明,假设我们起初没有债务。第一年末,我们赤字为100美元;第二年,赤字为200美元;第三年,赤字为300美元。这三年结束时,我们的债务分别为100美元、300美元(= 100美元 + 200美元)和600美元(= 100美元 + 200美元 + 300美元)。如果我们在第四年实现了50美元的盈余,债务就会减少到550美元。
凯恩斯教导我们,财政工具——即税收和政府支出——可以用于经济管理。当我们想要刺激经济增长时,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来实现;反之,当我们想要减缓经济时,可以采取相反的做法——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
决定财政政策是扩张性还是收缩性的,重点不在于赤字本身,而在于赤字的变化。考虑三种情况,假设我们从第一年开始就有赤字。在情况1中,在第二年中赤字与第一年保持完全相同;在情况2中,第二年的赤字进一步增加;在情况3中,第二年的赤字减少。
情况1——赤字不变:虽然如果政府支出的任何变化都完全与税收收入的变化相匹配,就会产生这种结果,但为了简单起见,假设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都在年复一年之间保持不变。这种结果既不是扩张性的,也不是收缩性的。尽管这种中性经济政策,赤字每年保持在同一水平,未偿还债务的金额将不断增加。
情况2——赤字增加: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赤字和债务都将增加。
情况3——赤字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经历一种收缩性财政政策,尽管债务仍将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将放缓。
尽管我们可以把赤字变化视为决定财政政策是收缩性还是刺激性的标记,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政策选择并不一定是确定性的。也就是说,不管财政政策的方向如何,整体私人经济很可能会起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财政政策可能产生一些微弱的收缩性影响,并不一定预示着经济活动将放缓。
凯恩斯教导我们要逆周期地使用财政工具,用以抵消失业率过高和面临无法接受的通货膨胀率时的经济不景气。然而,对于债务水平的担忧在凯恩斯看来只是次要的;但他在1930年代出版了他的论著时,联邦未偿还债务的水平要低得多。
如今,随着债务偿还成本占所有联邦支出的13%以上,许多财政保守派认为债务水平值得更多考虑。如果不加以控制,债务负担(即与债务相关的利息支付)可能变得难以承受。为了避免这一潜在问题,关切之人通常会希望看到作为财政刺激支出的资金随着时间逐渐被还原,尽管要逐渐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推动我们进入衰退。
从长远来看,自2000年财政年度以来联邦政府就没有盈余,这意味着自那时起,联邦债务每年都在增长。2009年大萧条后赤字激增,达到接近1.5万亿美元;但在此之后,赤字逐渐降至2015年约为5000亿美元,之后再次上升。然而,2020财政年度赤字真正激增,达到超过3万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新冠救助支出增加,但2017年12月《减税和就业法案》的通过也导致了税收收入的减少。
随着新冠资金基本上已在没有进一步拨款的情况下使用,2020年的历史最高赤字已有所回落;但它仍然较高,历史上来看,截至2024财政年度(截至2024年9月)超过1.8万亿美元。
2009年和2020年赤字大幅上升似乎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使用财政刺激的理念;但到了现在,未来赤字量已变得更加令人担忧。这些赤字的发展进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中规定的减税是否将于2025年到期,或者是否会延长,当然,这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
特朗普的承诺不在话下,但目前,再次审视2017年法案中最初通过的减税是否应该永久化,或者允许其到期并恢复至2017年以前的条款是合适的。个人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延长减税措施。考虑到当前的税收收入无法支付现有政府支出义务,与其面对目前如此繁重的债务负担,未经必要又增加债务,现在特别是债务负担如此高的情况下,似乎是不合适的。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来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历史上高昂的利息负担。在2024财政年度,联邦债务利息支出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因此,解决方法应是优先考虑努力降低赤字规模。增加税收和削减政府支出应该是一个可行方案;其中之一应包括允许2017年立法中的减税措施到期。这些措施不必一步到位,但理性之举应该能够设计出一些逐渐减少赤字的计划。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这一进程,同时我们正享受健康的经济状况,而引发衰退的可能性似乎很小。